艾米莉·狄金森说,我不怕那些喋喋不休的人,就怕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的沉默者,因为他一旦开口,就不凡。
郑丛洲就是这样一个忍隐在日常,但一张口就不凡的人。他从不标榜自己“在写作”,告诉别人写了多少散文、诗歌、文学评论和报告文学。但是,只要跟他坐在一起,只要他觉得你对文学有纯粹和诚恳的态度,他就会放松戒备,对你娓娓而谈。从古到今、从中到外,他都有见地,特别是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。从作家的为人到作品,都有深刻而准确的评骘,且不溢美,不饰非,耿直道来。因都是从文本出发,有在场及物的实证支持,即便听着有些逆耳,大多也无力辩驳,只有信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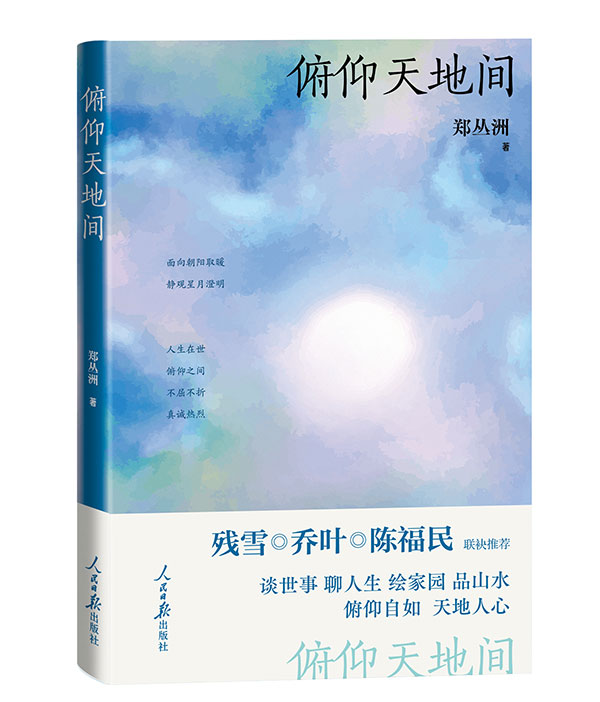
郑丛洲读的书太多,也太仔细,作家的代表作和名篇经典,他都能把关键的叙述和精彩的字句背下来。于是,他虽然两手空空、素妆而来,身体里却自带刀剑(学养),一旦涉险,便左劈右挡,瞬间变侠。他虽有“述而不作”的古风,但更多的是“不屑于作”的矜持。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年年作、月月作、天天作的写作狂人,作品虽多得成堆累案,但剥开包装,裸露处可入目者不多。读得太多,就有了钱基博式的定力,他心中自有一部《现代(当代)中国文学史》,再流行的作品,他也要衡以“我的”尺度,初读喜,再读疑,终读诋,经得住质疑和批评的作品,就真的好了!
正因为此,郑丛洲认为,我的长篇小说《美狐》是当代乡土创作的开创之作、圆熟之作,我便信以为真,便半夜鸡叫,给刘江滨、李林荣二友打电话,逼他们表态。他们从梦中惊醒,迷惑地问,哥们儿你是怎么了,是不是太寂寞了?我说,简单地说,我这部小说是不是很自洽?他们说,你凸凹不管小说、散文,还是评论,不都是很自洽吗?这还有什么可质疑的。我赶紧饶过他们,望着厚暗的天花板,就朗声独笑起来。所谓自洽,就是自我得意,自美。我一受用(感到舒坦),就独笑,所以,笑在我这里不是动词,而是形容词。
郑丛洲的这一册文字,也正是一部高度自洽的散文。郑丛洲的自洽之义就在于——
其一,破格局。一改当代散文,特别是区县散文一贯的“匍匐于乡土、醉倒于村俗”的低伏之态,让“自我”挺身,让“我思故我在”的语言之旗高高飞扬。因而,郑丛洲无拘无束,甚至不管不顾,恣肆运笔,任性挥洒,让文体无以界定,或曰诗,或曰散文,或曰随笔,或曰杂感,或者干脆就叫作:诗化散文、哲学笔记!
在技术层面,郑丛洲勠力于文字的“复合”品质——叙事、抒情、论理三者之间,不简单是一种因果关系,也不是一种被动服务的关系,而是结伴而行、共同到达。具体地说,叙事里有抒情,抒情里有叙事,即便是论理,也不是以传统样式靠叙事与抒情的铺垫最终得出结论,而常常是论理进入叙事和抒情环节,在交互作用中推动意象、意绪和意义的形成,以期达到浑然天成、无造作痕迹的效果。
其二,去浮尘。即把写作化作日常的生活动作,或者说,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这样一来,郑丛洲的文字就有了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的风致,并与我的《石板宅日思录》发生了遥相呼应的关系,因而我激动不已。我在《石板宅日思录》的自序中说道——
我觉得,日常生活太平凡,都是庸常琐碎之事,可记录者不多。或可以说,日常生活是一盘散沙,沙上不长禾苗,更不长嘉木,几无示人秀色。却偶有金屑,被掩埋其中。所谓日记,就是沙里淘金的努力,在无价值处提炼出价值,在无意义处升华出意义。记日记的企图,其实就是抵抗健忘和过分的凡俗,在“超越”的层面上有所作为,让人的生物存在,有灵魂的点点闪光。
所以,我的日记,不是俗生活的原生态记述,而是灵魂登场时的掠影,为的是把那些稍瞬即逝的片段定格,裨益于今后的生活。通俗地说,我的日记所记,是:记读、记思、记情、记趣、记悟、记痕。其中的记痕,可以是游踪,也可以是心路历程。
以此衡之,郑丛洲的散文,也不是俗生活的原生态记述,而是灵魂登场时的掠影,也是记读、记思、记情、记趣、记悟、记痕的产物。所不同的是,他更执着在“超越”上下功夫,有强烈的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情结,以至于他的每一段文字都有金句,而且不止一处金句,自然就会碰撞出铿锵复铿锵的重音,振聋发聩,醒人豁己。
其三,郑丛洲的文字有趣好玩。他很会运用“意象”“象征”“通感”“反语”,并且在小处看大、在近处看远、在虚处看实、在低处看高、在戏谑处看庄肃,从不主观强硬地确定意义。一不“确定”,反而让文字有了张力,引读者进入,共同完成那最后的意义。
在现实生活中,郑丛洲好酒、好交游、好嬉戏,也好放言,常充当说破皇帝的新装的那个稚童的角色。因而通透无邪,便远离一般作家的装腔作势、迂腐自执,情趣和气脉更与熊秉明、韩美林和黄永玉切近。
他的散文,虽然有草民的底色,但也展现了知识者独特的家国情怀、人文品格,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、东方智慧的精彩演绎。他的文字,集智性、灵性、悟性与人间性于一体,是其阅破沧桑、深味世事之下的人生经验的结晶与升华。他的笔下,没有风花雪月的轻薄,没有引经据典的枯涩,更没有堆砌辞藻的作态。清新流畅,自然率真;谈天说地,博古通今;涉笔成趣,浑然一体——我涵养着我、我推动着我、我成全着我,之后,再向旁人说话。因而常在调侃、戏谑、笑谈、反讽、幽默中,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和鲜明的个性。这一点上,大可以与韩美林的经典散文《闲言碎语》、黄永玉的《懒人闲思录》相对照、相媲美。
郑丛洲散文的完成,常常是在晚间的酒后,是具有独白品质的一觞一咏一斯文,因而最初命名为“酒后呓语”。我偶于半夜无眠时读到就被抓住魂魄,忍不住在大腿上狠拍了一下“好!”,之后,就天天在夜半里期待,以医治我的失眠之苦。他也真够哥们儿,真的源源不断地送来呓语。我觉得我也应该够哥们儿,便把拍大腿的私密动作,变成公开的点评,如隔空对酌,好让他发出更多的呓语。而且,几乎是他每发出一篇,我就点评一篇,乐此不疲,兴致盎然。累积下来,居然已有百余篇。给人的印象是,凸凹总是为郑丛洲啸叫不已,比所谓的铁杆粉丝还“无底线”。
没办法,郑丛洲的斯文写出了我心中想写而写不出的文字,我干吗不自信地自洽、干吗不自信地自美?本来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,想把我那些点评在这里罗列一下,但多少有些“说破”,有嚼饭哺人之恶劣,于是作罢。相望在两个人的共鸣、共情中,岂不更美!
是为序。
2023年7月20日
于京西昊天塔下石板宅
(作者为北京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、房山区作协主席、房山区文联原主席,本文为人民日报出版社《俯仰天地间》序言)
(《人民周刊》2024年第4期)
(责编:汪翠萍)

